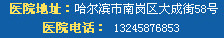崇祯帝日日夜夜为国家和社稷操劳,自己也是出了名的勤政节俭的皇帝,但是最后为什么还是沦为亡国之君?
他有一个重大的性格缺陷那就是缺乏担当精神,经常患得患失,屡屡错失最佳时机。
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件大事上,第一件是陈新甲议和泄密被诛杀,第二件是朝廷南迁之议一直拖着,直到明朝灭亡的前一刻都还没一个决定。
首先陈新甲议和泄密被诛杀事件。
后金(清)国在宁锦之战中失利之后,一时难以突破明朝花了大量人力财力的宁锦防线,决定开辟第二战场,从内蒙地区迂回进入明朝边塞,前前后后四次侵扰明朝内地,大肆在内地进行烧杀掳掠,劫夺大量财物和人口,一边用来强大自己的实力,也持续为明朝放血,消耗着明朝的有生力量,为突破辽东地区的宁锦防线创造有利条件。
后来后金国在义州屯兵,并逐步推进到锦州,终于在崇祯十四年包围了锦州。
崇祯帝急急忙忙命令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13万大军增援锦州。
洪承畴一直主张“必守而兼战”,也就是一边做好防守,一边寻机进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刚开始崇祯帝和朝廷同意这个稳扎稳打的计划。
但当农民起义再次磅礴发展,崇祯帝又希望尽快结束辽东地区的战争,以便集中兵力对付农民起义军。
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于是提出四路进兵、来个里应外合,合力围攻锦州女真军的方案,崇祯帝觉得可行,就密敕洪承畴进兵围攻。
洪承畴深知这一战完全就是天方夜谭,因为明军根本不可能在没有城池依托下能野战赢女真军,只能无奈将粮饷留在宁远、杏山与塔山西北的笔架山上,然后率领六万军队挺进塔山。
皇太极于是倾国而出,并亲自到松山督战,就是为了毕其功于一役。
果不其然,洪承畴被困在松山。
总兵祖大寿被围于锦州,屡次突围而不得出。
陈新甲与清朝议和就是这个背景下开始的。
为了挽救被围的洪承畴祖大寿和几万精兵,陈新甲在崇祯十四年十月提出了“息兵”之策。因为皇太极此时想要休养生息,派出使者准备和明朝议和,当时在宁远的宁前道副使石凤台,得到清军有意议和的消息,立马写信向清军将领询问是否属实,得到“此吾国素志也”的答复后,上报辽东巡抚叶廷桂,叶廷桂上奏朝廷。
崇祯帝内心是同意议和的,因为辽东之事已经糜烂,无可挽回,但他好名声,缺乏担当精神,过去曾经多次拒绝与清朝议和,现在一大败就求和,觉得有失面子,对自己名声是个巨大打击,于是斥责叶廷桂是“漫任道臣辱国妄举”,将石凤台逮捕下狱。
拖到年底,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已燃遍整个中原,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围困开封,清军也将松山团团围住。
内阁大学士谢升便与内阁大臣们进行商议,决定由陈新甲奏请与清朝再次和议。
崇祯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崇祯帝与陈新甲进行召对时,陈新甲婉转地向崇祯帝提出:“(松、锦)两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
崇祯帝一听,立马明白了“用间”的含义,回答道:“城围半载有余,一兵未能达,何间之乘?可款则款,可便宜行事。”
陈新甲明白了崇祯帝的意思,随即推荐兵事赞画主事马绍愉作为议和使者,崇祯帝即予允准,并“加绍愉职方郎中,赐二品服”。
但是,他还是觉得战败求和,有失天子的颜面,因此特地“谕新甲密图之”,要求绝对保密。
马绍愉于是领命出关,前往宁远,与清朝方面进行接洽。
清朝方面请以敕书为信。结果崇祯帝仍大摆天下共主对待边疆属夷的架子,以一纸“谕兵部陈新甲”的敕谕代之。
皇太极为此极为不满,也以敕谕英郡王阿济格等人的形式,要求明廷更换敕书。
马绍愉只得奏报朝廷,一来一回耽误了几个月的时间。
在这期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已先后被清军攻陷,洪承畴被俘虏,祖大寿投降,明军已经全线溃败。
崇祯帝得到辽东奏报后,仍以敕谕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形式,准其便宜行事,并派遣兵部司务朱济賫敕,同马绍愉前往盛京与清朝进行谈判。
皇太极提出了一系列的议和条件。
马绍愉返回宁远,立即派人向陈新甲禀报清朝方面的和谈条件。但和议的消息却被谢升无意间泄露,引起清流言官的慷慨陈词。崇祯帝信誓旦旦的说没有与清朝议和,并将谢升革职,以平息舆论。
不料,陈新甲收到马绍愉禀报议和条件的密疏居然也被泄露了。
一时间天下舆论大哗,言官弹劾如雪片一样多。
与清朝议和,原是遵照崇祯帝“可款则款”的谕旨推行的,谈判使者也是由他加官赐服任命的,辽东败局已经注定,如果崇祯帝勇于担当责任,以九五之尊站出来说明议和的理由,强行平息舆论一点都不难。
但崇祯帝却患得患失,只顾自己的颜面,下旨严厉苛责陈新甲。后遂于七月底将陈新甲逮捕入狱,并于九月二十二日将他斩首示众。
此时的皇太极已经休整完毕,不在需要议和,再一次率领大军攻破明朝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八十八座城池,掠走余口人和大量物资,再次给予明朝沉重的打击。
再说明朝迁都南京之议久拖未决的问题。
崇祯帝其实一直都在做准备南迁的准备,只不过都是在暗中,没有放在明面上来。
先是派遣给事中左懋第“往南中,察沿江舟师士马之数”。继而在崇祯十六年十月,天津巡抚冯元飏“密陈南北机宜,当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为来日迁往南京作好准备。
崇祯帝即下谕,让冯元飏“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备缓急”。
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在中原地区歼灭明军主力,并攻占西安,开始为东征作准备。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大顺国。
初三日,忧心忡忡的崇祯帝在德政殿召见左允中李明睿,征询“御寇”之策。
李明睿提出:“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
崇祯帝很是心动,就问道:“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亦未知天意若何?”
李明睿回答道:“上内断圣心,外度时势,不可一刻迟延,后悔何及。”
崇祯帝四顾周围无人,说道:“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
在当时形势下,迁往南京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
此时,长江中游驻扎着左良玉和江北四镇的重兵把守,只要崇祯帝在,他们就不敢在明面上反抗朝廷。
江南地区,又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人口最为密集的富庶之地,也较少的遭受战争的波及。如果退守南方,凭借南方充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北方抗衡,最后也能成为一个东晋或者南宋。
但是,迁都南京涉及到放弃宗庙陵寝的敏感问题。这就需要君主勇于承担责任,乾纲独断。
崇祯帝虽刚愎自用却又优柔寡断,死要面子却又怕担责任,只会说,不会做,李明睿一直劝崇祯帝早做安排,尽快安排,不可延迟一刻,崇祯帝却因为不想承担自己放弃祖庙的责任,期待文武百官劝说自己而在进行南迁。
但是以崇祯帝缺乏担当责任的性格,加上滥杀大臣,哪个臣子敢劝说崇祯帝南迁,劝说了,替崇祯帝挡了刀,以后也会被崇祯帝推卸责任,找理由给卖掉,还不如拖着。
于是,这件事就这样永久的被搁置下来。
左都御史李邦华为李明睿同乡,也是李明睿出任左允中的举荐人之一。李邦华担心南迁之议为朝论所阻拦,就提出由太子朱慈烺南下南京监国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的建议,请求崇祯帝明诏“遣皇太子监国南京”。
正月十八日,崇祯帝密谕首辅陈演:“宪臣言是。”
陈演一直反对南迁,故意将崇祯帝的消息向外面透露,从而引起文武群臣的议论纷纷。
李明睿觉得应该放手一搏,公开上疏朝廷,阐明自己南迁的主张。
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上疏斥其为歪理,扬言“不斩明睿,不足以安人心”。
李明睿上疏辩驳,谓:“唐室再迁再复,宋室一迁南渡,传国百五十年。若唐、宋不迁,又何有灵武、武林之恢复?又何有百五十年之历数哉?”
崇祯帝也召见光时亨,斥之曰:“一样邪说,却专攻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
崇祯帝依然没有任何担当,这时候就应该杀鸡给猴看,杀光时亨以儆效尤,南迁的反对力量至少减少一半。
二月,李自成统帅的大顺军进逼北京城。
二月二十七日,崇祯帝召集文武群臣,讨论战守之策。
少詹事项煜支持李邦华的建议,由太子监国南京。崇祯帝原本是支持这项建议的,但后来几经琢磨,觉得让太子前往南京监国,自己还是难以逃命,况且由太子监国,说不定会重演唐肃宗灵武登基的旧戏码,认为还是实行李明睿的皇帝南迁之议最为妥当。
第二天,他又召集内阁大臣,把李邦华的奏稿递给内阁大臣看,要大家表个态。
内阁大臣回奏:“昨东阁会议,有二臣亦主此议。”
崇祯帝大为恼火,却无可奈何,只能表示他将坚守京城,“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崇祯缺乏担当精神和滥杀大臣的恶果显现出来了,内阁大臣们都担心,皇帝南迁会留下自己辅佐太子居守,成为“死社稷”的成员之一;就算随驾南迁,一旦北京城失守,自己也会因为支持南迁,丢失明朝祖庙而代崇祯帝受过。
因此他们为了不成为替罪羊,只能一个劲地劝谏道:“太子监国,古人尝有,亦是万世之计。”
这下,别说崇祯帝,就连太子也走不了了。
当南路大顺军已经抵达直隶真定的时候,南迁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崇祯帝还在问战守之事,文武百官依旧沉默不语。
这才有了崇祯帝那句著名的言论:“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
这时候,崇祯帝便只有“死社稷”一条路可以走了。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zz/82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