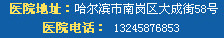屈原区汨罗庙祭祀屈原的历史,见证屈原区是汨罗的源头
汨罗庙因为建在渊北汨罗山上故名汨罗庙。它的前身是汉代所立此地的渊北屈原庙,唐后改称汨罗庙。
汨罗山是今凤凰山最西南端的一个山头,河泊潭(汨罗渊)北,旧为汨罗戍(驿)地,年围垦屈原农场后统称为了凤凰山。
磊石庙建在磊石,汨罗庙建在汨罗(渊),当然是天经地义的。
清《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湖广六明确记载:“玉笥山,在县北七十里,汨水西流经其下,有屈潭,亦曰罗渊,屈原放逐自投于此。隋置玉州,盖以山名。其相连者曰汨罗山,以下临汨罗江也。又磊石山……”此据说明汨罗山与磊石山中隔汨罗江,是“两山对峙”。玉笥山连汨罗山,汨罗山对磊石山,汨罗山在屈原潭的右边是无疑的。
《湘阴县图志》记汨罗山又名烈女岭,“西有烈女岭、图经谓之汨罗山。玉笥山。”说明西边的烈女岭才是汨罗山、玉笥山。而十二疑冢的烈女岭在凤凰局东部,《纪要》记载与《图经》记载是一致的。
《水经注》的地标从东到西是:罗城、罗水、玉笥山(玉洲治)、汨罗渊(屈原潭)、汨罗驿(历史上第一个汨罗地名)、磊石山。
《读史方舆纪要》从东到西的地标是:玉笥山(玉洲治)、屈原潭、汨罗山(汨罗驿)、汨罗江、磊石山,并统一在“县北七十里”一个地方。
所以这座汨罗山,正是《水经》所记的汨罗驿,正在汨罗渊北,此地之山头名为汨罗山也天经地义,汨罗山上屈原庙统称汨罗庙是完全正当的。
屈原汨罗庙是汨罗江人民纪念屈原而设立的地表建筑,汉至乾隆十九年它曾和屈原墓屹立在汨罗山上多年,与磊石山屈原庙、洞庭庙、黄陵山(湘山)黄陵庙遥遥相对,成为洞庭湖的一大景观。解读着汨罗江纪念屈原的悠久历史,见证汨罗江龙舟从沉江地汨罗渊飞跃到洞庭湖,流传全国。
汨罗江的屈原庙又名三闾祠(庙)、磊石庙、昭灵庙、屈原庙、汨罗庙、屈原祠、忠洁侯庙、清烈祠、屈子庙、屈子祠。
《湘阴县图志》记:“三闾祠在县北六十里汨罗江(指汨罗渊)者,相沿为汨罗庙。乾隆二十年,知县陈钟理改建玉笥山(东)上。其特祀于湘阴者曰汨罗庙。”
之所以把汨罗渊(屈原潭、河泊潭)北的屈原庙都统称为汨罗庙,是因为其建在汨罗渊北的汨罗山上。而汨罗本来就是“哀屈原”而特别取的名。屈原自沉的地方叫汨罗,故而其北岸的山称之为汨罗山、汨罗驿,因此而称之为汨罗庙。古代汨罗名就是一个潭名、渊名,是专门用来纪念屈原沉江一事的,故而光绪年前都没有把汨罗作为其它地方的地名,这是官方极大尊敬屈原的结果。汨罗渊上汨罗庙、汨罗渊北汨罗山,汨罗渊在罗城三十里地距的范围之左右,今天凤凰山河泊潭春江嘴是其中心点。
根据历代文献记载说明此处是“魂归于泉(汨罗渊),尸归于坟(屈原墓),灵归于祠(屈原庙)”三体同框的纪念屈原的正庙之地。古迹曾有汨罗庙、屈原墓、汨罗江(汨罗渊、汨罗、罗渊、故渊、河泊潭)、盘石马迹、凤凰台、屈原故居、宋玉招魂处、屈原塔、招屈亭、独醒亭、濯缨桥、渔父祠、女媭祠、贾谊吊屈台、司马迁泪涕处、笔架山、钓鱼台、剪刀池、绣花墩、秭归山、渔父潭(江潭)、玉溪(沧浪水)、龙船坝、白马井、江墓潭、南阳里、南岳庙、南阳寺、香炉湖、沉沙港、洞庭庙。共达30处之多。此处是古代一座完整的屈原文化公园,端午公祭屈原的正宗之地,解读了多年的汨罗江史,此地是纪念屈原的端午龙舟发源地。
总结历代汨罗山上屈原庙都有所特色体现。
1、汉、南北朝屈原庙
汉立屈原庙的标志是地点上有盘石马迹。
最早见于公祭汨罗渊北屈原庙的文献是南朝宋文学家颜延之为湘州刺史吴郡张邵“恭承帝命”重修屈原庙公祭屈原而写下的《祭屈原文》。
《祭屈原文并序》云:“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吴郡张邵,恭承帝命,建旟旧楚。访怀沙之渊,得捐佩之浦。弭节罗潭,舣舟汨渚。乃遣户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闾大夫屈君之灵:兰薰而摧,玉缜则折,物忌坚芳,人讳明洁。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温风迨时,飞霜急节。赢芈遘纷,昭怀不端,谋折仪尚,贞蔑椒兰。身绝郢阙,迹遍湘干。比物荃荪,连类龙鸾。声溢金石,志华日月。如彼树芳,实颖实发。望汨心欷,瞻罗思越。藉用可尘,昭忠难阙。”
颜延之(-年):字延年,南朝宋著名诗人。这篇祭文大约写于南朝宋少帝(刘义符)景平二年(年)。宋少帝即位后,傅亮、徐羡之专权,颜延之被贬为员外常侍,外放始安郡(今广西桂林一带)太守。颜延之在赴任途中,经过汨罗渊,代湘州刺史张邵作此祭文,有《颜光禄集》。
“访怀沙”二句:意为来到屈原投江之处。屈原投江前曾作《怀沙》,有“怀沙砾而自沉兮”之句,罗潭:指罗渊;舣:停泊。汨渚:汨罗渊边。时间地点记载得清楚明白。从此据表明,汉代所立在汨罗渊北的屈原庙,在颜延之的努力下得到重新修建。也同时说明其后《异苑》《水经》所记渊北有屈原庙并非虚言。
刘敬叔(?—)《异苑》记:“长沙罗县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净,异于常处。民为立庙在汨潭之西岸侧,盘石马迹尚存,相传屈原投川之日,乘白骥而来。”汨潭指汨罗潭,盘石马迹位置在河泊潭川江嘴今名春江嘴,即《水经注》所云汨罗(戍)山东、屈潭之左玉笥山西。当今凤凰山上了七十多岁的老人均亲眼见到过此盘石。
这块盘石马迹不但是建庙的物证,同时也是屈原居住在此地玉笥山的物证,因为马迹形成必须经历一定的岁月才可见其痕迹。可知渊北屈原庙东的屈潭之左边就是玉笥山。
从《楚辞》《哀郢》可知,屈原迁南方是乘船而来,说明他平时在罗地使用的白马是罗子国提供。
北魏郦道元(年~年)《水经注》也云:“罗渊北有屈原庙,庙前有汉太守程坚碑记。汉未犹存。”这碑是庙碑还是墓碑?历代也有过探讨,没有形成结论。
按道理,屈原沉江于此,尸体在此打捞上岸,立庙立墓在此也是天经地义之事。如果尸体没有打捞上来,在此立衣冠冢也为天经地义之事。
所以唐蒋妨云:“魂归于泉,尸归于坟,灵归于祠,为其实。”故而这块石碑应该为屈原墓碑。
2、唐代汨罗庙
唐代渊北屈原庙的特点是“正庙以渔父配享”,说明汨罗庙唐未成为正庙。
唐诗人皎然(—年)曾来汨渚写下《吊灵均祠》一诗,其云:“昧天道兮有无,听汨渚兮踌躇。期灵均兮若存,问神理兮何如。”磊石山位于湘水之中,如果写磊石屈原庙,则不会着“汨渚”二字。见证唐天宝七年的唐代汨罗渊北屈原庙。
《湘阴县图志》记:唐天宝七年(年),玄宗敕所在忠臣自傅说而下十六人,置柯宇致祭长沙郡楚三闾大夫屈原,定名汨罗庙,内设渔父祠。
此庙重修以后唐诗人纷纷到汨罗渊吊屈原,应成一种风气。
唐张翔(—)《经罗渊吊屈原》云:“谠言忠谏阻春霄,放逐南荒泽国遥。五梦楚兰香易染,一魂香水渺难招。风声落日心逾壮,鱼腹终天恨未消。却借微香荐蘋藻,海门何处问渔樵?”
唐李嘉祐《夜闻江南人家赛神因题即事(年前后)》诗云:“南方淫祀(祠)古风俗,楚妪(媪)解(能)唱迎神曲。……听此迎神送神曲,携觞欲吊屈原祠。”
诗中所说“淫祀(祠)”是指南方喜欢建寺庙;从汨罗江的庙宇来看众多,也是个证明。“屈原祠”说明汨罗渊屈原祠的确有其建筑。
唐诗人第一次直写“汨罗”的诗是杜甫《天末忆李白(年)》:“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但杜甫这年没有到汨罗(民国前的汨罗,均指汨罗渊)。
他晚年到汨罗是公元年,他那年在汨罗庙写下《祠南夕望》:“百丈牵江色,孤舟泛日斜。兴来犹杖屦,目断更云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杜诗说》云:此近体中《吊屈原赋》也。结亦自喻。此借酒杯以浇块垒,“山鬼”、“湘娥”,即屈原也;屈原,即少陵也。说明此诗是汨罗渊吊屈原的诗,祠就是屈原祠汨罗庙。
唐褚朝阳(年登进士第)《五丝》诗云:“越人传楚俗,截竹竞萦丝。水底深休也,日中远贺之。章施文胜质,列匹美于姬。锦绣侔新段,羔羊寝旧诗。但夸端午节,谁荐屈原祠。把酒时伸奠,汨罗空远而。”此诗也出现汨罗渊北屈原庙的身影。
唐清江(年南阳从慧忠习禅观)《湘川怀古》诗云:“潇湘连汨罗,复对九嶷(一作疑)河。浪势屈原冢,竹声渔父歌。地荒征骑少,天暖浴禽多。脉脉东流水(一作去),古今同奈何。”清江说明屈原冢在汨罗渊,浪能到墓,说明墓距汨罗渊在10--20米之间。但此诗不见庙,很有可能此庙此时已荒废。
这是可查的最早写屈原冢的诗,写到的地点在唐代的汨罗,就是汨罗渊,“浪势屈原冢”,汨罗之浪能泊向屈原冢。如此之地理环境,十二疑冢处不可见,因为此地离罗水有二公里、距今汨罗江有三公里。而汨罗渊北汨罗山就在江边、南北总宽度才一里不到。
中唐孟郊年到汨罗写有《楚怨》:“秋入楚江水,独照汨罗魂。手把绿(芰)荷泣,意愁珠泪翻。九门不可入,一犬吠千门。”诗中无庙、坟的踪影,也无暗示,可能看的是汨罗水。
唐贞元二十年(年)韩愈到汨罗自沉渊,此时汨罗庙已经荒废,他写下《湘中》一诗:“猿愁鱼踊(一作跃)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蘋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蘋藻满盘无处奠”正是此地的荒凉之景,连屈原墓都难寻找,从孟郊诗看,至少荒废十多年了。
唐太和二年(年),袁州刺史蒋防赴任途经汨罗渊,应邀作《汨罗碑记》:唐文宗太和二年春,防奉命宜春抵湘阴,歇帆西渚。邑宰马搏谓予曰:“三闾之坟,有碑无文,岂前贤缺欤?”又曰:“俗以三闾投汨水而殒,所葬者招魂也,常所惑焉。”按《图经》,汨水冬二尺,夏九尺,则为大水也。古之与今,其汨不甚异也。又楚人惜三闾之才,闵三闾之死,舟驰楫骤,至今为俗。安有寻常之水,而失其遗骸哉?安有不睹其骸,而知其怀沙哉?但以楚词有大小《招魂》,后人凭而穿凿,不足征也。愚则以为三闾魂归于泉,尸归于坟,灵归于祠,为其实。郡守东海徐希仁洎马搏,以予常学古道,熟君臣至理之义,请述始终符契,以广忠贤之业云。於戏!后代知予者以此,罪予者以此。文曰:屈碑立兮,谗人泣兮。屈碑推兮,谗人咍兮。碑兮碑兮,汨之隗兮。天高地阔,孤魂魄兮。
西渚,就是西水;汨水,就是汨罗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汨,长沙汨罗渊。”汨是汨罗渊的简写,也就是屈原潭、河泊潭,地点很清楚。此记说明蒋防祭新庙后,就在汨罗渊将屈原墓碑竖起。
《湘阴县图志》记:唐蒋防汨罗庙碑记。“案,……碑云屈原之祠有碑无文,《三闾大夫志》作屈原之坟。玩其下文云:俗以三闾投汨水而死,所葬者招魂也。尝以憾焉,极辨招魂葬之诬。《铭辞》亦云:‘天高地阔孤魂魄兮’,始终不著庙祀之义,似属墓碑。”
《元和郡县图志》记:“屈原冢,在县北七十一里。”考湘阴隋唐县城地距正在春江嘴处的汨罗山。唐杜佑《通典》载:“罗江有屈原冢,今有石碑,文为‘楚放臣屈大夫之碑’,其余字灭。”唐代的汨罗就是汨罗渊,江是罗江。唐代并没有把汨罗叫成汨罗江。
中唐诗人贾岛年写有《送郑长史之岭南》:“云林颇重叠,岑渚复幽奇。汨水斜阳岸,骚人正则祠。苍梧多蟋蟀,白露湿江蓠。擢第荣南去,晨昏近九疑。”“骚人正则祠”他知道汨罗渊有屈原祠,说明他亲历了此地。此诗可以说明蒋防到此地时不但树了墓碑还重修了汨罗庙。
晚唐崔涂(年前后在世)《屈原庙》诗云:“谗胜祸难防,沈冤(一作魂)信可伤。本图安楚国,不是怨怀王。庙古碑无字,洲晴蕙有香。独醒人尚笑,谁与奠椒浆。”“庙古碑无字”按《舆图部汇考四十一》唐十五记:“(湘阴)县北有汨水,即屈原怀沙自沉之处,俗谓之罗江。又有屈原冢,今有石碑,文曰楚放臣屈大夫之碑,其余字灭矣。”此据明确说明唐代汨罗渊北有屈原庙,又有屈原冢,可知此诗写于汨罗渊北汨罗庙。
唐末至五代韦庄(约年-年)《鹧鸪》诗云:“南禽无侣似相依,锦翅双双傍马飞。孤竹庙前啼暮雨,汨罗祠畔吊残晖。秦人只解歌为曲,越女空能画作衣。懊恼泽家非(一作知)有恨,年年长忆凤城(一作皇)归(懊恼泽家,鹧鸪之音也)。”此诗明显看出充满郑谷《鹧鸪》诗的味道,黄陵庙、汨罗庙一一道来。此诗可证明马殷修磊石庙时(年),此渊北屈原庙还基本完好,所以马殷没有重建渊北屈原庙。
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记祠庙三闾庙:“屈平沉沙之处曰汨罗江,在岳州境内,正庙以渔父配享,唐末有洪州衙前军将题一绝云:苍藤古木几经春。旧祀祠堂小水滨。行客谩陈三奠酒。大夫元是独醒人。”写明唐未的三闾庙在沉沙处,宋始,沉沙地被首名为汨罗江。
沉沙处的屈原庙内有唐人洪州衙前军将题诗,作者是谁找不到历史记载,但是唐人无疑。“正庙以渔父配享”则说明唐未汨罗庙内增设了渔父祠,是唐代汨罗渊北(河泊潭)屈原庙的鲜明特点。
3、宋代汨罗庙
“右为庙左为冢”的特点从宋代屈原庙记中突显出来。
宋代屈原庙除《方舆胜览》记载宋屈原三闾祠在沉沙处外,宋张舜民(年进士)《画墁集》卷八加记了距离磊石山的地距,记:“东岸始有人烟,曰龙渥(磊石山龙窝),…有水自东出,曰归义江口,入口十许里余即汨罗也,一水中分南曰汨,北曰罗,洲上有忠洁侯庙即三闾大夫也。”十许里正是磊石山到河泊潭春江嘴的距离。与《荆州记》“屈原潭去罗县三十里”地距东西两个方向压缩了一个大约三里多水路的汨罗渊区域。汨罗山也正好三里多长。所以宋代屈原庙定位依旧在汨罗渊北的春江嘴汨罗山上。
宋范致明((?—年)《岳阳风土志》也记:“青草湖在垒(磊)石山,与洞庭相通。其南罗水出焉,故罗县在其上。其东汨水出焉,下有潭,谓之屈原潭,屈原怀沙自溺之所,忠洁侯三闾大夫庙在其上。”宋代屈原庙明确记载在汨罗渊河泊潭北。
王定民(哲宗元祐中年知湘阴县)《书碑阴》记:“怀沙而投于江流,湍疾救晚而失其骸,皆不见疑也。与申徒狄负石何以异,而蒋防于此疑之,是疑其无有也。湘人思之,招魂而葬。于是墓起于江,之于葬能藏其棺衾,而不见貌。于是有庙以祭之,祭以思其貌。邑有庙者三,以见湘人思之多也。”“墓起于江”说明此处有屈原墓,“邑有庙者三”,这是指磊石山、汨罗山、湘阴县城均有屈原祠(或指称此地的屈原故宅南阳寺可能奉屈原香火,被后世认为南阳寺为旧屈子祠)。
《古罗志》录鹤山魏了翁(—)《新修汨罗庙歌》:“鸾皇栖高梧,那能庙鸱枭。椒兰自昭贤,不肯化艾萧。人生同一气,初有善不善。一为君子归,宁受流俗变。云何屈大夫,属意椒兰芳。兰皋并椒丘,兰籍荐椒酱。……”云:此诗系过归乡沱祠下所作,前记用以为歌,故并载之。
宋淳裕八年(年),胡哲《重修汨罗庙记》云:“县北五十里为汨罗江,原之正庙,故冢在焉。谓安得访汨罗之滨,……始至之日,固有以庙地当正,庙宇当新。”“两山对峙,一水萦回,是为汨罗。其右为庙,其左为冢。”两山是指汨罗山(今凤凰山西南汨罗驿)、磊石山。磊石山与汨罗山相隔一个汨罗渊,清越南使者阮宗奎乾隆年记:“昔屈原别号三闾大夫沉于此,其坟与庙去江三里路。”两据都说明庙与墓均在一起,河泊潭春江嘴地也正好离旧时湘江三里路,与上面数据合一。据《湘阴县志》记载:汨罗书院建于宋大中祥符年间,在汨罗庙东,后以其地建汨罗庙。
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二十三》记:“屈潭在湘阴县六十里。郦道元水经云:汨水西经玉笥山又西为屈潭,即罗潭也。”“图经今有屈原冢在江侧或谓楚人招魂葬焉,又有屈大夫碑而字灭无迹矣。”记载清楚明白,庙与墓在一个地方。
罗含《湘中记》云:“屈潭之左有玉笥山。”宋彭淮诗云:“汨罗水绕三闾宅。”此诗之水是磊石山东的汨罗渊之水,南有汨罗江、北有白塘湖、西边就是汨罗渊磊石港。凤凰山正是在这片U形水的包围之下,“两山对峙,一水萦回”“汨罗水绕三闾宅”,非常生动地概括了本地之地理形态,至今可见。
魏良臣(--)《汨罗庙》云:“清白声华正直风,数千馀载誉增隆。侯封忠洁缙绅外,庙外汨罗烟霭中。新宇有功脩已顿,旧碑无字读难穷。他年我若官湘楚,愿采遗言问钓翁。”这个汨罗实际指凤凰山和磊石山之间的大水域,水雾、水汽蒸发的时候,的确也如烟霭,“旧碑无字”又回到《水经注》所说渊北石碑上。
北宋释德洪在大约在公元年受贬后到汨罗渊写下《和曾逢原待制观雪》一诗,其云:“魂清寒妥贴,寺近汨罗江。”这个寺应指南阳寺,这个年代南阳寺就在屈原故宅出现了,是很有可能的。说明宋代突然出现南阳名,跟这个南阳寺是有关的。“近”说跟历史记载玉笥山后汨罗渊有关,因为宋《方舆胜览》已经定论:“屈平沉沙之处(汨罗渊)曰汨罗江”。凤凰玉笥山(今玉笥山下是罗江)靠近汨罗江,上面的南阳寺当然也近汨罗江。
宋胡哲云(年前后)云:“清烈公正庙,在南阳汨罗江”,南阳在这里首次出现,南阳指屈原故宅,说明南阳在汨罗江(实指渊)这个地方。而旧传南阳设过屈原庙,应指潭左玉笥山上的屈原故宅。山之南名阳故曰南阳是很合理的。旧南阳庙应是楚人罗人共同的先祖祝融之庙,今天此山上还有南岳庙,屈原居住于此,是很有道理的。屈原沉江之后,传说设立过屈子祠,当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宋绍熙年间,真德秀(—年)继朱熹守潭州,这年端午节恰逢朱熹启动的修缮汨罗庙工程竣工,他亲临汨罗渊,主持了竣工典礼,撰写了《祭屈原文》,主持了祭屈大典。
其文:“德秀之后先生也,盖千有馀祀。而于《离骚》《九章》,一读一兴叹焉。甚哉!先生之忠于国也。世降俗末,媚佞成风,过其祠者,可以厥颡矣。德秀虽无似,愿师其人于千载之上。视事之发始,敢不告虔。履洁含忠,益当自勉。胡吉侯抱忠贞而不遇兮,嗟无路以叩阍。困行吟于泽畔兮,志于邑而莫伸。托《离骚》以纾怀兮,慨想乎唐虞之君。处沟世而若谗兮,甘组豆于江神。葬鱼腹而不悔兮,洁瓣香而招魂。伊南阳之故里兮,祠妥灵而若存。界一江之相望兮,暮木拱而轮困。昔疆界之广袤兮,窘侵攘之纷纭。熟厘正而使归兮,量予力而征单。欲东走于长安兮,言惧卑而莫闻。惕朝思而夕念兮,莫慰侯于九原。荐菲奠于正祠兮,撷涧沼之频繁。希御风而下降兮,鉴予意之动拳。”
“伊南阳之故里兮,祠妥灵而若存。界一江之相望兮,暮木拱而轮困。”中“南阳故里”说得明白,就是屈原故居。他站立的地点在汨罗渊,这是在屈原潭边上的玉笥山,不是有二十里之距的清代屈子祠玉笥山。一江指屈原潭后到磊石山的汨罗江,“暮木”指汨罗庙边的屈原墓周围的林木。祠在,汨罗渊下的屈原“灵”就会归于泉而存,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明代由于将南阳寺迁入了翁家洲,南阳名也先后被应用于这一带的南阳里,南阳街、南阳埂、南阳渡,给不明真相的后人留下了想像空间。清史者居然不考察南阳名只有可能见于山南而不会到罗水北的事实,南阳吉里,也只有可能是称玉笥山系的山南。释德洪说寺近汨罗江,南阳就肯定是“屈原故里”之名,屈原不可能居住在罗水包围之中的沼泽之地。
从“南阳汨罗江”来看,翁家洲前的河流宋代仍然称之为罗水或归义江,所以此南阳指屈潭之左玉笥山之南阳故里,是无疑问的。宋代并没有出现疑冢说,所以这是进一步说明屈原墓与汨罗庙在一起。
端明大参高定子(年-年)《新修汨罗庙记》:“明仲恢庙墟故址而新之,其知所当事矣。”则是再修建汨罗渊北汨罗庙的记载。
南宋赵汝谠(?—)《屈原祠》云:“采藻或涧滨,茹芝亦岩阿。下将从彭咸,终已投汨罗。湘水碧湛湛,湘山郁峨峨。昔存怀沙恨,今见垂纶过。”此诗所写地理环境在汨罗渊。
赵希鄂(年知湘阴县)《汨罗庙》诗:“怀沙一死固堪伤,千载修名实未亡。举国无人君不悟,斯文有幸日争光。谗言枉以艾萧恶,正论终归兰芷香。解印欲辞罗水去,祇倾罗水奠离觞。”汨、罗两水在故渊复合,就成了汨罗水了,所以是辞罗水。
旅游地打造构想图
宋诗人许晟大(湘阴人,年为湖南提点刑狱)有《汨罗庙》诗:“白鹤真人朝玉京,故留仙属镇山精。时人却道投潭死,不得其平所以鸣。”也说明庙在汨罗潭。
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二十三》记:“图经今有屈原冢,在江侧,或谓楚人招魂葬焉,又有屈大夫碑而字灭无迹矣,贾谊渡湘为赋以吊原,史迁亦尝经此水。”
宋代汨罗庙记无可争辩地说明,汨罗江名始于宋代,指的是汨罗渊,南阳名起始于宋代,指的是凤凰玉笥山屈原故宅,屈原墓进一步确定在汨罗渊北的汨罗山上。
4、元代汨罗庙
元代汨罗庙东有南阳寺是元代屈原庙特点。
元致和元年(年),刘行荣《重建忠洁清烈公庙记》云:“祠产甚丰,为南阳寺僧所据。泰定甲子(年)州守宋仲仁春卿籍其产归祠,新其殿宇。明年,孙天才元质来继守,庙东创斋舍……据此记是宋淳枯八年,至此八十年中,祠产一侵于豪民,再侵于南阳寺僧,专恃地方官清理。今其碑尚存(墓碑),文字剥蚀多不可辨。《三闾大夫志》亦稍有修补,略存其概,以备参考。”“今其碑尚存(墓碑),文字剥蚀多不可辨。”很显然,这是渊北汨罗庙无疑。
此据是归“祠”,而不是归“寺”,说明重建的不是南阳寺而是屈原汨罗庙。从上据来看,元代出现南阳寺全名,推论是将汨罗山旁边的玉笥山屈原故宅改建成了南阳寺,所以南阳寺僧能非常方便地占据汨罗庙资产。如果弄到相隔三十多里地的明清翁家洲的南阳寺来占据汨罗庙资产,似乎没有这种可能。
清《湘阴县图志》在汨罗书院字条中明确记载:“刘行荣《汨罗庙记》:‘庙东仍创斋居,为庖舍供膳享。’是书院,旧建汨罗庙东。(宋淳裕八年)。有南阳古市,有万岁潭。《楚南水道考》:‘凤凰台下万岁潭,相传赵宋先人水葬于此。因名。’”所以元代汨罗庙建在河泊潭是无误的,南阳古市也说明是因南阳故居而名,河泊潭因此也有南阳之称。说明南阳指的是屈潭之左玉笥山之地。
元范梈(年-年)《屈原庙前观雨,雨止,渡口观鱼》云:“乍来倏去峰前雨,半落未开沙际花。春远客怀淹燕雀,年荒民命假鱼虾。徒闻黄霸能为郡,岂识张骞苦泛槎。早谓仙人无世虑,山深往往饭胡麻。”
相传南阳古市就是渔街,故也有渔街市之称。是洞庭湖渔民鲜鱼集散地,一直到清朝均是如此。
张孝祥的《磊石》诗也云:“天气水云合,人家罾网间。晚来风更熟,别浦棹歌还。”金·赵秉文《伯时画九歌》云:“楚乡桂子落纷纷,江头日暮天无云。烟浓草远望不尽,翩翩吹下云中君。九歌九曲送迎神,还将歌曲事灵均。一声吹入汨罗去,千古秋风愁杀人。”元末明初刘基《竹枝歌其四》云:“潇湘江水接天河,第一伤心是汨罗。斑竹冈头兰蕙死,黄茅垄上艾蒿多。”
元末明初滕毅《三闾大夫祠》云:“下有栖神宇,惨淡临江濆。行吟既不返,遗响宁再闻。”
“临江”解说了汨罗庙的地理。
磊石山旅游点打造构想
5、明代汨罗庙
查找明代屈原庙的记载,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屈原墓与屈原庙相对,同样说明庙与墓是在一起,说明这不是远距离相对。同样说明汨罗山就是汨罗庙所建之地,位置就在汨罗渊河泊潭的春江嘴。
《明一统志》记屈原墓“在汨罗江与原庙相对碑额题曰三闾墓。”这与唐宋资料记庙与墓在一起的记载一致的。
《长沙府志》记汨罗庙“在汨罗江上县北六十里,《水经》曰:渊北有屈原庙,庙前有碑,今废。洪武二年(年),知县黄思让重建,有濯缨桥,独醒亭,奉旨复号楚三闾。大夫屈平氏之,神命有司,以五月五日致祭屈原。于唐封昭灵侯,于宋封忠洁侯。”此据说明是在渊北重建汨罗庙,有濯缨桥,独醒亭。而濯缨桥又是玉笥山连接汨罗山的标志性建筑物。
明史谨(洪武中谪居云南,以荐为应天府推官,迁湘阴县丞)《屈原庙》诗云:“江边遗庙掩松筠,檐际云霞互吐吞。地接武关龙去远,枭临阿阁凤难存。湘兰日老春风佩,楚些谁招月夜魂。留得生前诸制作,千年光焰烛乾坤。”此诗可见证此时的屈原庙。
夏原吉(-)《谒三闾祠》云:“先生见放事何如,薪视椅桐梁栋樗。忍使清心蒙浊垢,宁将忠骨葬江鱼。西风楚国情无限,落日沧浪恨有馀。我拜遗祠千古下,摩挲石刻倍欷歔。”说明宋代磊石庙成为行祠后,萧振《三闾庙记》所说的“摩挲石刻”,也许都集中到了汨罗庙。
明陈贽(—1)《三闾庙》云:“湘水流无尽,江蓠烟雨深。古祠人罕到,鶗鴂怨春林。”
明嘉靖二十年(年),戴嘉猷《重修汨罗庙记》记:“始克修祀事于汨罗(渊)。……忠节清烈,如我公是处仅专祠焉,祀废不知几何年矣,……适有以南阳僧舍,数多所宜拆毁,请相去甚迩。遂发公帑馀金,命邑幕袁宪董其役,募夫徙建。凡为门、堂总若干楹,稍加涂饰,焕然一新。……摩挲断碑,乃知是庙元泰定间知州事宋侯春卿重建,并黜南阳僧徒归所侵地。去今二百余年,庙再新焉。”
此记是南阳寺迁建的重要说明,“拆毁”的是“僧舍”,就是南阳寺。“徙建”的当然也是南阳寺,也可以说拆除南阳寺的东西,重修屈原庙。僧舍指僧人的住所也指寺院。南阳寺就是这次迁移到翁家洲的无疑,屈原故宅的牌子也跟了过来。“重修汨罗庙”说的不是迁建汨罗庙。后世误读此记,认为屈原庙,跟南阳寺一同迁建到了大洲。是没有弄懂“稍加涂饰,焕然一新”之意思。重新迁建一座汨罗庙“稍加涂饰”也是做不到的,此句说明汨罗庙并没有迁建,而是作了一番装修而已。“摩挲断碑”“去今二百余年,庙再新焉。”说的是装修一新罢了。“黜南阳僧徒归所侵地”,如果是迁建何必来此举?说明汨罗庙地仍然在元代的地址之上,说明重修的是刘行荣所修复的屈原庙。元代屈原庙在汨罗渊,那么此次的庙也依然在汨罗渊。
明嘉靖(年—年)《湘阴县志》记:“汨罗庙,在汨罗江,洪武二年知县黄思让建庙前建濯缨桥、独醒亭。祭日以五月五日,盖原沉江之日也,后人哀之。”然后自蒋防起,历史修建汨罗庙的历史呈现于此字条后。未着一字说明汨罗庙是迁建了。沉江处叫汨罗江,汨罗庙当然还在沉江处。翁家港是罗水、罗江。所以南阳寺并没有建过屈子祠,这就很清楚了。此志“南阳寺”字条也记:“在南阳渡,奉汨罗香火。”说明南阳寺此迁建到了南阳渡,因有“屈原故宅”匾额,内奉屈原神像,是可能的,当为行祠使用,并非正庙。却被清光绪史者误记为屈原旧祠,也是没有读懂戴嘉猷的《汨罗庙记》。
明梁辰鱼(约—约)《屈原庙》云:“寒云掩映庙堂门,旅客秋来荐水蘩。山鬼暗吹青殿火,灵儿昼舞白霓幡。龙舆已逐蜂头梦,鱼腹空埋水底魂。斑竹丛丛杂芳杜,鹧鸪飞处欲黄昏。”
明李之世(年举人)《过汨罗吊三闾庙》云:“昔闻楚子怨,今过汉江湄。山鬼搴萝立,湘灵鼓瑟悲。茝兰行客荐,时俗土人思。古庙空山里,阴风闪翠旗。”汨罗就是汨罗渊,不是南阳渡,也说明明代三闾庙还在沉江地是无误的。
崇祯二年(年),余自怡《重修汨罗庙碑记》记云:“三闾故有祠在汨罗,去湘治七十里。崇祯二年己巳,吏于下湘。考《图记》:汨罗在治北。……及问先生祠,则云自吾新安戴黄门前峰先生修葺后,至今缺然矣。……予同士民捐金三百两,命良民黄一凤董其工,逾月告成。”此汨罗不是指今天的汨罗,是指河泊潭汨罗渊,说明汨罗庙在汨罗渊北之汨罗山没有变动。
明末清初陈子升(—)《三闾庙》云:“汨罗沈自昔,安问后人怜。古庙临湘水,秋兰薰楚天。”汨罗山就在湘水之中,可证。当然此诗可能也写磊石屈原庙。
明末清初白胤谦(明崇祯十六年年进士)《湖南纪行》云:“沙边三闾庙,无人垂橘柚。山鬼护幽忠,仿佛存遗构。”沙边说明此三闾庙地理位置不在磊石山,而在汨罗渊。
《湖广通志二》记载:“汨罗山,在县北七十里汨罗江畔,上有屈原墓;玉笥山,一名石帆山,在县北七十里屈潭之左,┈┈”“汨罗江在县北七十里,汉书《地理志》:┈┈屈原自沉处。”汨罗山、屈原潭、玉笥山均在一个方位,一个距离“县北七十里”,均在河泊潭周边。
《湖广通志十三》:“汨罗山在县北七十里汨罗江畔上有屈原墓”“玉笥山一名石帆山在县北七十里屈潭之左。”《大清一统志》三十六卷记也载:“汨罗山,在湘阴县北七十里孤峙汨罗水中。”明代的汨罗依旧指的是汨罗渊。
明苌燧《三闾祠》云:“荒祠落落枕空江,千古沅湘姓字芳。楚国孰知皆醉梦,先生独肯为纲常。可怜疑冢非初意,却信丹丘是故乡。兀坐青毡怀往事,寒鸦几点下斜阳。”这首诗是首提汨罗庙边屈原墓为疑冢的诗,十二疑冢的传说也许从此时开始。明嘉靖《湘阴县志》在汨罗庙字条后也录入此诗。在屈原墓字条后,说明“屈原墓即汨罗山”,附王庄诗两首,一首说汨罗江畔屈原墓,一首说青草城东屈原疑冢。
明末清初屈大均《湘阴作》云:“青草三闾墓,黄陵二女祠。风清闻玉佩,云暗见兰旗。湖口潇湘阔,天边鸿雁迟。容颜殊姣好,公子未曾知。”磊石是青草湖的地标,湖口正指的汨罗口,确证屈原庙、墓在磊石山东的汨罗山上。
明嘉靖《湘阴县志》和清张廷玉所编《明史》卷四十四记也载:“屈原墓,即汨罗江(指渊)畔。有碑曰三闾大夫墓。王庄有诗:孤坟云寒猿叫断,荒祠日暮鹤飞回。《离骚》三复情何限,谩采苹花奠一杯。”“疑冢,在青草城东。王庄诗:疑冢何劳苦用心,没堆青草独相寻。屈原只葬江鱼腹,留得香风直到今。”但两首诗同现,则是有否定疑冢之意的。
青草城指的是古罗城。疑冢在罗城东北方位基本也是对的。说明王庄先到了汨罗渊屈原墓,又到了疑冢。否定了疑冢的存在。所以十二疑冢的传说,最早源自明嘉靖年间(年—年)。
今人被修水而来的今世泛指的汨罗江说法误导,又被六六年的汨罗布局了迷魂阵,均不知道古代所说的汨罗指的就只是汨罗渊一个小地方,屈原自沉的汨罗,是水也是地;汨罗江也只是沉沙处的一个称谓。汨罗庙建在汨罗驿、汨罗山才可称汨罗庙应该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罢了。
明唐伯元(—)《送何侍御谪官之楚(改代稿)》云:“乾坤几见三闾庙,词赋难招万古魂。明过湘江回首处,贾生才思不堪论。”此诗将贾谊吊屈原自沉渊的故事放入诗中,此庙也当在汨罗渊。
明末清初岑徵(—)《湘阴谒三闾庙》云:“遗像缘虫篆,空廊污燕泥。浮湘魂不散,归郢路长迷。帝子山如黛,王孙草又萋。千秋有遗恨,长在武关西。”这首诗见证汨罗庙的荒废。
6、清代汨罗庙
清代汨罗山上屈原庙的特点是“去江三里路”。
清乾隆《湘阴县志》载:“汨罗山在县北七十里,汨罗江出其下,上有屈原墓。”《湘阴县图志》记:“以五月初五日致祭,曰三闾祠。案,自宋时立庙县城,名三闾行祠,致祭皆于汨罗庙。雍正九年(年),重建屈子祠,加春、秋二祭。于是春、秋祭于县祠,其汨罗庙仍以五月初五日致祭,祭仪并同。凡黄陵、汨罗、三闾三处,共支祭费银八两。”这个屈子祠指湘阴县城行祠,这个汨罗依然是汨罗渊北的汨罗正庙,说明此庙完好。同时也说明磊石山和临泚的屈原行祠都不再有祭屈功能。
清越南使者阮宗奎《吊三闾大夫》诗题云:“舟自阴湖(湘阴)进发,经龙鸟(乌龙)嘴乃汨罗江故道,昔屈原沉于此处,其坟并庙去江三里,逓年端午日,楚人竞渡龙舟以吊之。”诗云:“彩鹢凌波水暎窗,罟师报道汨罗江。骚人何处秋兰咏,渔父空横午笛腔。云积愁思还淡荡,波涵忠愤故舂撞。悠悠风韵三千载,浩气犹留五月艭。”
作者阮宗奎(-),号舒轩,越南太平御善福溪人,乾隆七年(年)、十三年(1年)两次使清,早于汨罗庙迁移时间年的8至12年,“沉于此,其坟并庙去江三里路。”说明故渊地有汨罗庙。可以充分证明陈钟理所迁的“故渊”汨罗庙还在河泊潭春江嘴上的汨罗山,此地离汨、罗复合口三里,离湘江也正好三里。说明“三里路”的地距记载是无误的。
旧时磊石山、凤凰山均在湘水之中,两山西隔磊石山大约七里多,围垦农场后这儿建有八里堤(实七里),春江嘴离磊石山十里,说明汨罗山离湘水三里,正好证明阮宗奎所记不误。
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一年(-1),陈钟理《重修汨罗三闾大夫祠记》云:“……甲戌春,奉天子命来令湘阴,公馀访三闾沉渊故处,旧有祠,为湖水浸啮,垣瓦仅存,榱桷将圮。……今仅一专祠,顾任其颓败不振,微特非所以妥忠魂,亦非所以振人心而厚风俗也。余咨嗟久之。爱与诸生登玉笥,四山啾啾,犹闻啼啸声。乡士告余曰:‘此当年作九歌地也。’盍迁庙而祀于此。遂属周生富榜、黄生齐植、高生峻、杨生茂根等董其役,鸠金一千有奇,饬工庀材,徙三闾祠而新之,宏而甚丽也。其前为骚坛,又其前为独醒亭、招屈亭,又其前为濯缨桥。经始乾隆甲戌八月,竣工乾隆乙亥九月。庙成,诸生丐余言志其颠末。余以祀发生为教忠之大者,爰刻石而为之记。”
此记明确说明屈子祠是从“沉渊故处”移建,迁的是三闾祠,不是屈子祠,此地在哪?“沉渊故处”就是故渊。《湘阴县图志》云:“盘石马迹,在川江嘴(今名春江嘴),即古汨罗渊也。”也就是“去罗县三十里”的河泊潭汨罗渊。仅一专祠,说明磊石行祠也没有祭屈原了。“独醒亭、招屈亭、濯缨桥”是汨罗庙前的建筑;骚坛是此次移庙增建。
《湘阴县图志》记:骚坛,乾隆二十一年,王立槐有记。邑人黄德然建。
周韫祥诗云:“一卷《离骚》万古心,千秋坛坫此登临。江声北控荆门壮,云气西连峡口深。三户兴亡空慨叹,《九歌》哀怨未销沉。我来欲续沧浪曲,坐对烟波思不禁。”
湘阴县城行祠此年也可能荒废,屈子祠继承的是河泊潭汨罗庙衣钵。此据也说明汨罗庙始终在河泊潭汨罗山上,不存在明代迁移到南阳寺的说法,更不存在此庙旧地址无考之说。
《湘阴县图志》记载:同治六年(年),黄世崇《重立楚三闾大夫墓碑记》记:“《通志》及《明一统志》记载甚详,汨罗山为今烈女岭,亦非解地,历二千余年并无疑冢之说,不足辨也。”并在凤凰汨罗山上重立楚三闾大夫墓碑。
根据《长沙府志》和《湘阴县图志》记载,迁庙自乾隆十九年开始,将汨罗庙和汨罗庙周边的濯缨桥、独醒亭、招屈亭也一同移建到此。汨罗书院地宋代建为了汨罗庙,故而此记没有移建书院的记载,骚坛在此地增建。
清姚椿(--)《屈子祠》云:“荆楚邱墟废,湖湘日夜流。异朝余涕泪,同姓托危忧。败壁难为古,寒花易感秋。征途循枉渚,浩荡驾螭虬。”
此诗说明汨罗庙因为离开了汨罗正地,故而文人们按规矩改称了行祠称谓屈子祠,虽然此时此庙仍然称汨罗庙或者三闾庙。
同治八年(年),乡贤集资修缮,并更名为屈子祠,书法家虞绍南重书唐、后梁、宋、元碑文补刊祠内。
清末民国初释敬安《九日过屈子祠》云:“野径斜云上绿苔,经过此地不胜哀。千年感慨遗湘水,万古离骚识楚才。泽畔行吟还忆昨,庭前谏草已成灰。我来浊世怀高洁,不奠黄花酒一杯。”
7、清立屈子祠
屈子祠前身是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一年从河泊潭汨罗渊北汨罗山上所移建的汨罗庙,又称屈原庙、屈原祠、三闾祠、三闾庙。汨罗庙(河泊潭渊北屈原庙)始建于汉代。屈子祠始建于乾隆十九年,其室内文物均来自磊石庙、汨罗庙和屈子庙。其景点濯缨桥、独醒亭、招屈亭、屈原故宅、汨罗书院、剪刀池、绣花墩均从凤凰汨罗山、凤凰玉笥山上移建或移名而来,骚坛原生地在此地,乾隆年间所建。明后有楚塘传说、十二疑冢传说等发生在此地。
屈子祠东南距汨罗市城关10多公里,距古罗城8公里,西距屈原沉江地汨罗渊10多公里。位于玉笥山东部的一个山头,古罗江、今汨罗江北岸。与古罗城、晒尸墩隔江而望。
这里古木参天,风景清幽。从山脚有石阶直登山顶。
屈子祠坐北朝南,一幢清朝风格的庙宇式建筑,巍然屹立在东玉笥山顶。
大门边刻着清诗人张文敏“万顷重湖悲去国,一江千古属斯人”的对联,正门“屈子祠”三个苍劲的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门额上饰有17幅反映屈原生平的浮雕。屈子祠整个建筑占地平方米,有三进三厅堂,十四耳房,大小天井七个,花坛四处,厅、堂、廊、池错落有致,浑然一体。
从正门而入的大厅壁下嵌着司马迁撰的《史记·屈原列传》的雕屏,上方挂着“光争日月”的横匾,两侧是清代文人李元度撰写的楹联:“下官吏,彼何人,三户仅存,忍使忠良殄瘁;太史公,真知己,千秋定论,能教日月争光。”“江下峰青,九歌遥和湘灵曲;湖南草绿,三叠频招宋玉魂。”(原屈子庙联)
在此厅山墙的南北两面,用花岗石刻有宋代苏东坡及现代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撰写的对联。人们穿过芬芳的金桂花坛后,便到一祭祀厅,厅中放着‘故楚三闾大夫屈原之神位’牌,左吊巨钟,右置大鼓,厅柱上挂有清代文人、外交官郭嵩焘撰写的楹联:“哀郢失孤忠,三百篇中,独宗变雅开新格;怀沙沉此地,两千年后,唯有滩声似旧时。”(原屈子庙联)
穿过圆拱门,进里是后厅,这里矗立着一尊高大的屈原塑像,屈原手抚佩剑,翘首昂视。塑像两侧,悬挂于立群手书的郭沫若集《离骚》句:“集芙蓉以为裳,又树蕙之百亩;帅云霓而来御,将往观乎四荒。”
厅两侧的厢房,已开辟为展览室,介绍了屈原的一生及对后世的影响;陈列了屈原著作的历代版本和后人研究屈原著作的成果。同时,这里还展出了屈原故里遗址和罗子国墓地出土的楚文物。这些文物揭示了两千多年前屈原被放逐在南楚汨罗江一带的社会状况。”人们来到屈子祠瞻仰,无不被屈原那种忧国忧民、上下求索的精神所感动,受到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8、清立屈子庙
清朝同治十二年(年),平江商人在李元度主持下又在河泊潭修建屈子庙。不过其地址已经在玉笥东大约两里多的一个山头,今河泊潭立碑处。
李元度当年发起平江籍商贾仕子捐款,在这里购置土地,修建码头,新建屈子庙。一为纪念屈原,二为船只货物中转方便。此庙由平江县各盐号捐金购地,修建屈子庙,兼作商会公所。拥有两艘万担大船、五十艘千担中船以及几百条木船的平江商会,终于独掌梦寐以求的河泊潭码头。那是凤凰山最热闹的日子,湖北开艕、宝庆毛板、宁乡乌杆、平江木船纷纷鱼贯驶入平江港抛锚停泊,屈子庙祭祀香火兴旺。又一度成为纪念屈原的中心。
屈子庙为砖木结构,所有建庙材料,均由平江县运来,每块青砖上均印有“平邑”二字。其建筑规模与结构均仿玉笥山屈子祠,正门较屈子祠略高,进申稍短,亦为三间三进。正门上方竖嵌“屈子庙”三个大字的青石门额,门两侧刊嵌青石刻成的张文敏撰字联:“万顷重湖悲去国,一江千古属斯人”。左右侧门上分别刊嵌“冰清”“玉洁”青石横额。三门的上方横排八幅堆画(学名石灰塑),均以传统戏剧故事为素材,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为方便来往船只夜晚进出,正门前立有一高高的旗杆,每到夜晚便将点燃的灯笼升至杆顶,以起导航作用。进正门为一宽敞高大的戏台,戏台上方为一八角藻井,藻井内龙盘凤翔,戏台前是石坪,两侧有跑马廊与后进连接,中进正中是一座硕大的四角亭,名“信芳亭”,取《离骚》中“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之信芳”之意。
亭由四根通天石柱擎起,石柱上一面有郭嵩焘撰联:“哀郢矢孤忠,三百篇中,独宗变雅开新格;怀沙沉此地,二千年后,唯有滩声似旧时。”另一面有李次青撰联:“上官吏,彼何人?三户仅存,忍使忠良殄瘁;太史公,真知己,千秋定论,能教日月争光。”(此二联在年屈子祠修复时悬于祠的前厅和中厅)此庙中进与两侧廊,平时为囤积货物之处;上进为神殿,供有“楚三闾大夫屈子之神位”牌,神位左有关公(财神)像,关公像两侧有关平、周仓像;神位右有女媭(屈原女,当地奉为送子娘娘)像;左右各悬钟鼓;出后门有一片小小的花园。
清李稷勋(年进士)《晚泊青草湖》写在屈子庙诗:“芦笋初生蕙叶滋,夕阳芳树屈原祠。白云不尽伤心色,洲渚青青二月时。”
屈子庙与屈子祠于年同时公布为湖南省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惜屈子庙却于年当成“四旧”而拆毁。
屈子庙拆毁后,其文物大多收入屈子祠。屈子祠保留年至今,成了汨罗江屈原文化遗迹中唯一的地表古建筑。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zz/46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