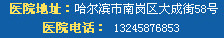□徐新民
田老师的工作,在野外的田间地头。田姓,在田间地头劳作,这就有点意味了。
田老师,个不高,黑黝黝的方正脸,头发有点粗有点硬,两眼炯炯,坚毅的目光直透前方。腰板很直,像极了立在野外的测量标杆,又正又直。
田老师在清理安吉八亩墩的绿松石饰品
田老师的手先天性控制不住的微颤,如果发掘新石器遗址,清理遗迹遗物时,担心微颤的手不小心碰着易损器物,使器物受到损伤。所以,那年毕业分配进考古所,做田野考古的四人中,三个人做新石器考古,唯有田老师选择商周考古。
田老师在清理安吉八亩墩的绿松石饰品
第一次去田老师发掘工地学习,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田老师参加发掘的土墩墓工地在长兴的林城镇。我从城站乘火车前往长兴,再转公交车到林城镇,然后步行。出发前,与田老师约好,大概中午时分到工地。
结果意外发生,那天,晃荡晃荡的火车声把我晃进了梦乡,直到乘务员查票,迷糊中看到长广站的站台,哎呀,坐过站了。交罚款、补票,下车,买票,等下一趟返回杭州的车次,在长兴站下车。
转公交,下车,往田老师工地走去。林中小道,老远看见田老师站在那里,两手交叉搓于胸前,焦急地张望。我不住地解释,田老师啥也没说,催促我赶紧吃饭。饭后,田老师带我看了发掘土墩墓的现场,我们聊了好多,细细听我的烦心事,轻声宽慰我。
曾与田老师、胡继根老师去武义县出差,那时还没有高速,到处在修公路,到武义要五六个小时,中途在东阳停车吃饭,下午才赶到武义。没有公款宴请,自己在政府招待所用餐。晚饭时,我和田老师买了一瓶四特酒,两人慢慢地对饮起来,慢慢地聊着,我不会劝酒,田老师也不会劝酒,他只会往自己酒杯里倒酒。或许,长途汽车劳顿,结果两人愣是没把一瓶四特酒喝完,这不是哥俩的酒风酒量。胡老师经常嘲笑田老师和我,没有传说中的那酒量。反驳不了,认账!
吉林大学84考古班在吉林市西团山遗址调查实习。前排左一是田老师
田老师喜欢每天喝点酒,刚开始是白酒,后来是黄酒。自发掘八亩墩后,爱上喝老百姓自酿的米酒,那酒,醇厚,有股米香,巡回在齿间。每当傍晚工地收工,大伙儿围在一起晚餐,田老师总是站起来,先为大家斟酒,最后给自己倒满一杯自酿米酒,说着白天工地上发生的事。端起满满的酒杯,田老师的手颤好像暂停一般,杯中酒绝不会晃出一滴酒。
年初夏,我在安吉溪龙乡发掘上马坎遗址,田老师在安吉笔架山挖土墩墓。有一天,他电话我,说他那里有旧石器出土。赶紧的,放下电话,找车就奔去笔架山的工地。果然,燧石质的双刃刮削器,长约3厘米、宽1厘米,加工精细。做商周考古的田老师,找到了一个旧石器地点。这个线索不能放过,第二天,我就安排吉林大学硕士生李有骞去做试掘。
9月8日,为配合申苏浙皖高速公路建设,我从安吉上马坎工地转移到长兴的七里亭遗址发掘。没多久,田老师结束笔架山发掘,也来到七里亭。当然,他还是发掘土墩墓。我们同住一个自然村,两个工地经常相互走动,喝点小酒。偶尔有人提议打个麻将,轻松一下也可。
田老师稳坐桌前,不管顺境还是摸了臭牌,看不出田老师的脸色异样。同事传说,一旦田老师摸了好牌,手就不颤抖。我一直观察他,等他手不抖时抢先胡牌,结果从没等到他手不颤抖的时刻,他胡牌了。我们认输认输。
牌局结束,田老师喜喜地不紧不慢说:“明晚来喝酒,酒钱我出!”然后,双手左右直摆,头也不回,步出门去。
七里亭的土墩墓发掘结束,田老师又转回安吉发掘土墩墓,工地在高禹镇的开发区,与长兴泗安镇紧挨。两镇地貌一样,同样的有旧石器地点。这一次,田老师在安吉发掘土墩墓,一挖就是十多年,从没离开过安吉。发掘上千座的商周时期到汉六朝的各类墓葬,需要极大的耐心和韧性,寒冬酷暑,风里来雨里去,从没听到田老师的怨言和抱怨。安吉博物馆库房里,修复完整的坛坛罐罐,按墓葬单位整齐地码放在文物架上,它们在说着以前的故事。历史,在考古人手中,有时会渗出苞谷烧的泥土味。
年年底,田老师开始发掘八亩墩,一个巨大无比的土墩,占地8亩。开工不久,去过八亩墩,墩上杉树林砍了,露出环壕和墩的尊容,气势庞大非凡,当时就想,要拿下这么大的考古工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务随时不请自来,主持者须得有相当的定力和气度。
田老师在清理八亩墩的陪葬墓
年11月,纪念张森水先生去世十周年活动在安吉香溢大酒店举行,刚好八亩墩发掘专家论证会同时同酒店举行,在酒店大堂巧遇来参加八亩墩论证会的陕西考古院师妹。晚餐,两个会的专家不在一起用餐,我客串去八亩墩论证会用餐房间,发现不见陕西考古院的师妹专家。一问田老师,他一拍自己脑门,一心专注会议内容,竟忘了告知师妹晚餐时间。如果不是师妹,真的溴大了。
八亩墩被盗过几次,墓内随葬品的损毁情况不明。艰辛的考古发掘,没有让大家失望,墓内棺底发现了大量的绿松石饰品。11月17日,遵田老师嘱咐,我陪同中国地质大学的杨明星老师来到八亩墩发掘现场。好久不见,田老师额头的皱纹又深些了,好似田里犁耕后的犁沟。整个下午,田老师实在太忙,抽出大约半小时陪杨老师观察绿松石。
飘扬的八亩墩考古队旗帜。徐新民 摄
傍晚,工地收工,田老师执意到城里和我们一起吃饭。他飞快地骑着电驴,回到出租房,安顿好母亲。母亲眼睛看不见,田老师把母亲从老家接来身边照顾。又飞驰而来,与我们一同去安吉城里。
看到这里,大家一定明白了,田老师是我的同事,没错。他还是我大学同窗,在寝室排行第七,我们亲切昵称他“田七”,不是《本草纲目》里的田七,是我们寝室的老七。
哦,差点漏了,田老师的大名叫田正标。田字,不偏不斜,标标正正。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zz/4362.html